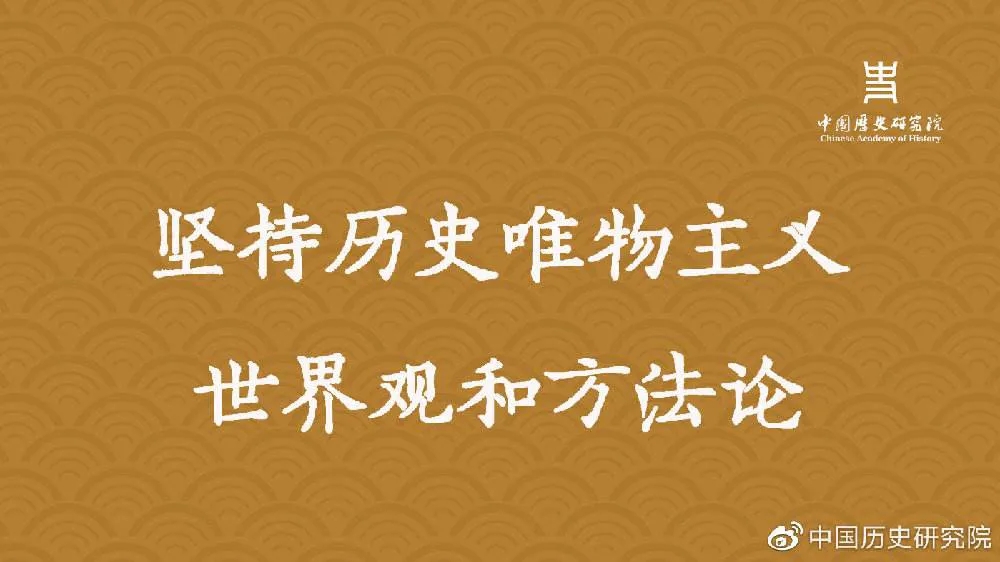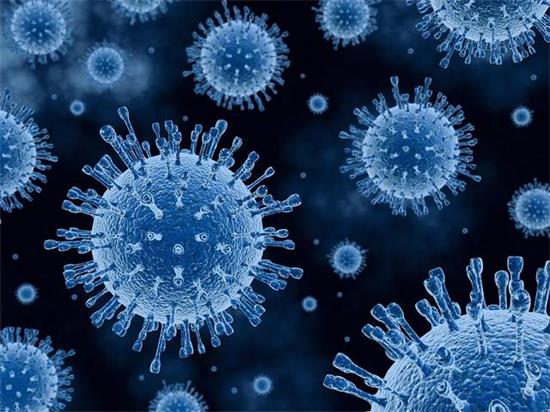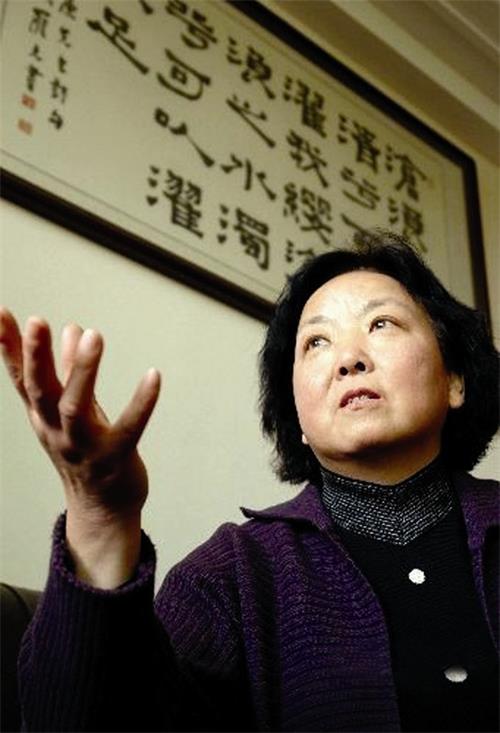一些史学研究者把所发现的某一个村庄、某一座庙、某一个舞厅、某一个饭店、某一本家谱、某一份“必须”错缺的地图、某个“足够”另类的乡贤的回忆,塑造成自己心中的敦煌,无限中心化其发现的价值,而其所在的时代、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重要政治变迁、历史性事件的过程和震荡、经济社会的宏观变化,被策略性回避。于是,跑马圈地,成为一些人的狂欢,把“邻猫生子”、别人无从置喙,当成绝学。史学在自我堕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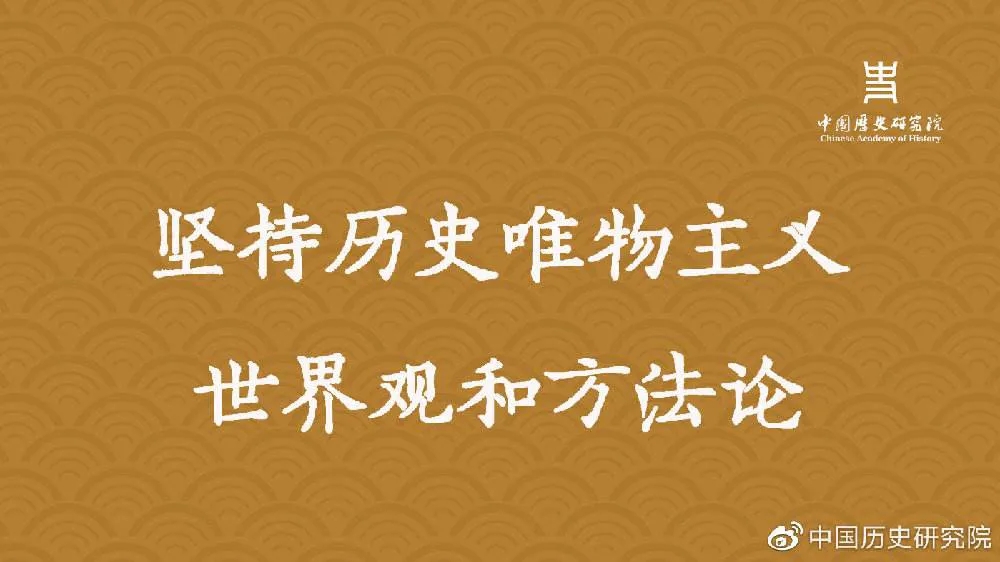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论断,是习近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此作的新的申说。
然而,历史研究也在不断遭遇挑战乃至危机,这是历史学反复跌入谷底又凤凰涅槃的契机,但应当明了其中很多危机是史学家亲手“制造”出来的,又必须由史学家亲手终结。历史和历史学家互相成全,又互相考验乃至敌对,在相互诘问中,历史学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碎片化”是当下中国史学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碎片化”不成其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这种意见并非没有共鸣,但现有的众多论说表明,大多数人将其视为“问题”。例如章开沅说:“‘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他主张,“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钱乘旦直陈“碎片化”为史学重大危机,认为,“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何为“碎片化”?成因何在?为何成为问题?穿行于“碎片”之中的中国历史学应当如何?对此均有反思和论述的必要。
一、碎片、碎片性和碎片化
因为名词之间暧昧难明的联系,新近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开始立论,难怪多斯自诩该书“已成为众多立论的源泉”。其实,无论问题提出之背景,还是所涉问题形成之过程,抑或是批评的对象,还是对史学未来的期许,当下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碎片化”和多斯当年所指,均非一事。
但多斯对年鉴学派第三代沉溺于描绘和叙述,失去总体性、整体性、通贯性追求,甚至剥夺人类在史学研究中核心地位的批评,和中国史学界近来面临之情势有很多共同之处,语言的“所指”和“能指”错舛而奇特地构合,也算一景。在中国史学界,“碎片化”作为问题的提出,先于“碎片”,因为前者是“问题”,而后者不是。但因为语言逻辑的关系,诸多论家多从确定历史研究必须依赖“碎片”即史料开始铺陈。李金铮说:“从主观愿望上讲,每一个历史学者都可能希望对历史现象‘一网打尽’。但由于人类社会极其复杂,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历史内容进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选择具体,选择碎片。”罗志田说:“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在此语境下,史料是“碎片”,史料即“碎片”,所以,从历史哲学层面上讲,历史研究无法回避“碎片”。自然,“历史是一个巨系统,即使是这个世界一天的历史,要穷尽其中的所有,历史学家也是无能为力的”。历史研究确实是在无数“碎片”中穿行,但从逻辑上却无法得出历史研究应当“碎片化”的结论。“我们迄今赖以研究历史的证据可能确实是历史身上抖落的‘碎屑’,但我们既然可能从一个细胞中找到隐藏生物体全部秘密的基因,从这些‘碎屑’中找到历史传承的规律也非痴人说梦。”相对于历史本体而言,史料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碎片性”,无碍于历史学家实践自己的伟大使命——“究天人之际”,是空间维度;“通古今之变”,是时间维度。在万古江河沧海桑田之变中,史学家力图把握其中的结构,透视其间的因果,总结其中的规律,以为镜鉴。司马迁为史学家厘定的任务,抓住了人类作为生活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中智慧生物的本能。正因为如此,从全球史角度看,史学几乎是所有文明摆脱蒙昧之后的第一门精神性创造。然而,“碎片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已成事实。李长莉说,“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考虑到李长莉的学术背景,以下的批评尤其直率:“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回顾多斯对“碎片化”史学面目的描写,对照当下中国史学界的某些现象,是时时让人会心一笑的——“历史学家对一切都表现出好奇,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公认价值的负面、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史学家把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和人为的转折抛在一边,而唯独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同样,人们在描述村庄、妇女、移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时,也赋予其一种新的美学形态”;“放弃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从社会退缩到象征性的文化”;“人类的脉动被归结为人类生存的生物或家族现象:出生、洗礼、结婚、死亡”。 中国“新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李长莉总结为“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在当下的史学实践中,一些史学研究者把所发现的某一个村庄、某一座庙、某一个舞厅、某一个饭店、某一本家谱、某一份“必须”错缺的地图、某个“足够”另类的乡贤的回忆,塑造成自己心中的敦煌,无限中心化其发现的价值,而其所在的时代、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重要政治变迁、历史性事件的过程和震荡、经济社会的宏观变化,被策略性回避。于是,跑马圈地,成为一些人的狂欢,把“邻猫生子”、别人无从置喙,当成绝学。史学在自我堕落中,“失去了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原料’”。
很清楚的逻辑是,史料的“碎片”性质,并不是“碎片化”研究的理由,当然也不是其成因。然而,新近的讨论中,无意中出现了一对误读:因为史学研究依赖于碎片性的史料,所以史学研究自然会“碎片化”;“碎片化”其实就是微观化、精细化。如有论者说:“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在比较成熟的西方史学界也许存在,在当下中国大陆史学界,我们的微观研究现状远未达到需要警惕细化的程度。”这种替代,在逻辑中是需要仔细辨别的。
从微观入手,对历史材料进行条分缕析的精细研究,是把握大历史、解决大问题的必要前提。梁启超评价明末清初学者阎若璩的历史性贡献:“《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梁启超称阎若璩的研究“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阎若璩经考证而宣判“古文尚书”的死刑,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其由“碎片”而始,却非“碎片化”指向,这在中外史学数千年演化历史中,实为百变常新的奥妙之一。事实上,即使是最严厉的“碎片化”批评者,也没有谁否定精细微观研究之价值,所以继续相关名词之纠缠实无必要。笔者认为,“碎片化”的成因,首在时代变化所引起之史学变化。多斯在论述年鉴学派日益流于“碎片化”研究时,分析了时代变局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结构主义也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下风行起来,人种学的意识激发了对其他文明的关注,人们对这些社会的抵抗力、稳定结构和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产生了兴趣。对‘他者’和人类真相的发现动摇了欧洲中心论。生活在别的空间的他者也上升为一种典型。”中国当下的“碎片化”成因不同于此,它直接肇因于先前过度用力的不当做法,即把几乎所有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于几个问题,忽视了历史非线性的复杂化和多层次。有论者回顾了某一时期近代史研究中排他性叙述框架的形成及其缺失:“政治史的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其实,不光近代史如此,整个历史学界都曾被限定在有限的议题内。“碎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一现象的矫枉过正,乃至渐入歧路。其次,史学家对近代以来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掌握不足,从而削弱了把握整体历史发展的思维能力,在“碎片化”研究的“小确幸”中自承无力,耽美于“小知识”的自我审美。史学启蒙时代为后世垂范的大家,几乎掌握了当时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知识,宏观处,通天彻地;微观处,芥子须弥。以《史记》言,内纳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而其中的八书记天文、历法、礼、乐、音律、封禅、水利、财用等,更有今日整体史的大模样。以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言,九卷皇皇,其前半部,全面阐述地中海东部西亚、北非及希腊地区约20个古代国家的自然地理、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历史变迁、风土人情;其后半部,主述波斯人和希腊人数十年间争战传奇。其取材之丰富,结构之宏大,取向之总体,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祖述于此也不为过。而今天之史者,确实可以归因于知识的海量积累和增长,总的来说,只能围绕专业掌握有限的知识。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近代以来物理学、天文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哲学含义,在史学界传播甚微。即使是习惯尝鲜的美、欧史学界,也不再能看到可以媲美前贤如牛顿、笛卡尔、玻尔、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兼思想家,几乎无人深究海森堡“测不准定理”“薛定谔的猫”、波粒二象性、“双缝实验”等的人文底色和哲学深度。无力感不仅充斥年鉴学派后人的心灵,也逼迫中国某些史学研究者在严厉的量化考核和荣誉追逐中急切地寻找出路,并把自身的“碎片化”研究正当化,在“逃跑”和“躲避”中致“碎片化”研究泛滥而渐成灾情。“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事实上,问题主要不在于这些东西被纳入研究对象,而在于一些研究者把这些当作了历史研究的主旨和乐趣。最后,特定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某些社会史研究范式被神话,并对“经典”作了拙劣的模仿。王晴佳直陈:“我们探讨国外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要探究新文化史的兴起”,他认为,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的一种反弹,是历史研究“碎片化”的主要表现。池子华等人则认为“碎片化”问题适用于整个社会史。到底是仅仅在新文化史研究中,还是在整个社会史研究中,或是在“新兴史学”中,抑或在整个历史研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乃至严重到以“危机”相论,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就“始作俑者”而言,多斯是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提出“碎片化”概念的。他对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崇敬自不待言,对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罗代尔也赞佩有加,并将其和第三代的“碎片化”研究作了区隔,“布罗代尔本人始终不忘史学的基础,而他的继承者们则早已将此抛在脑后。布罗代尔在研究中重视总体性、时间参照的统一性、各层次现实间的互动性和社会史的地位”。这一论述序列表明,多斯所说的“碎片化”主要指曾经“收编”了其他诸多学派,以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年鉴学派,在以历史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一些人中出现了游移和堕落。中国当下的“碎片化”研究,显然没有这么复杂的谱系,它更像是反复出现的“一窝蜂”式史学“热点”。而且,这种“热点”是对新文化史名著诸如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文化和阶级》、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金兹堡的《乳酪与虫子》、达恩顿的《屠猫记》等著述的拙劣模仿。当然,考虑到中外史学的映射互动关系,目前出现在国外史学中的一些“碎片化”研究所蕴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值得警惕。如有国外研究者“关注”贩卖黑奴过程中当地黑人、北非人的“作用”,有人研究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中拿鸦片当药品使用的“风俗”,等等。其“高级”的意识形态蕴含,说明某些人的所谓“新清史”研究并非孤立现象。
三、中国史学对“碎片化”的应有态度
如何走出“碎片化”研究?钱乘旦提出的要点是“体系”,“不管历史学家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李先明等人提出,“碎片”是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选择有“历史意义”的“碎片”进行研究。李金铮诉诸“整体史”,提出“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王学典等人则直接主张“重建”历史的宏大叙事,他们认为,“碎片化”背后衬托着当前史学界宏观思维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
笔者认为,对“意义”的追求,是人类所有学问的内在禀赋。意识流式的“碎片化”研究,对于破解某些故作高深的高头讲章不无微功,却消解了史学的特征和使命,并将历史研究化解为用美丽的腔调和轻曼的结构讲细碎故事的技巧,有迷失在如汪洋大海、漫天雪花却永远只是“碎片”的史料之中的可能。“史学家如果不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繁琐考辨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珠玑,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时贤提出的各种角度诊治“碎片化”的方案,在在均见对史学未来的关切。同时笔者想提出,要拒斥“碎片化”,须了解历史的特性——人物、事件、整体的社会,在想象的“静止”状态中,必定处在一个三维“空间”结构中;但加上历史的本质——“时间”维度后,它就成为“时—空”四维结构,这种结构赋予历史整体性和延续性。“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也是历史存在和演进的方式。布罗代尔扬言要将“历史时间”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及“个人时间”区分开来,实际上,在人类产生并将整个世界对象化以后,所有的“时间”都不可分,且弥散、结合于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是我们理解所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都是三维生物,但他们拥有值得骄傲和珍惜的技能,即理解四维“时—空”结构历史的能力。视野、观念、框架、模式、体系、理论等,广义地、长时段地讲,是历史学家介入历史的工具和方法。解读、阐释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研究“意义”产生的过程,而且这些“意义”必须在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延续性特征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说明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应当拒斥“碎片化”的。拒斥“碎片化”,须明了历史学是“人”的学问,史学的中心,必定是人。人的历史活动有三个方面的事实:其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其三,“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而且,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的“普遍交往”逐步发展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的全球化,使得“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新的含义,决定全球史时代的历史学,必须有普遍联系的观念。“碎片化”研究对此无能为力。“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的总要求,需要中国历史学界作出回应。中国有5000年以上延绵不绝、不断更新升级的文明史,构成人类史的宏大篇章;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更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多个层次螺旋递进的发展跨越,其实践和认知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历史学家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机遇和鞭策。“碎片化”研究也许还未成气候,却应当终止了。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原载《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昆仑策网】微信公众号秉承“聚贤才,集众智,献良策”的办网宗旨,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一个发现人才的平台,一个献智献策于国家和社会的平台,一个网络时代发扬人民民主的平台。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让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
特别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2、本站属于非营利性网站,如涉及版权和名誉问题,请及时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做相应处理;
3、欢迎各位网友光临阅览,文明上网,依法守规,IP可查。